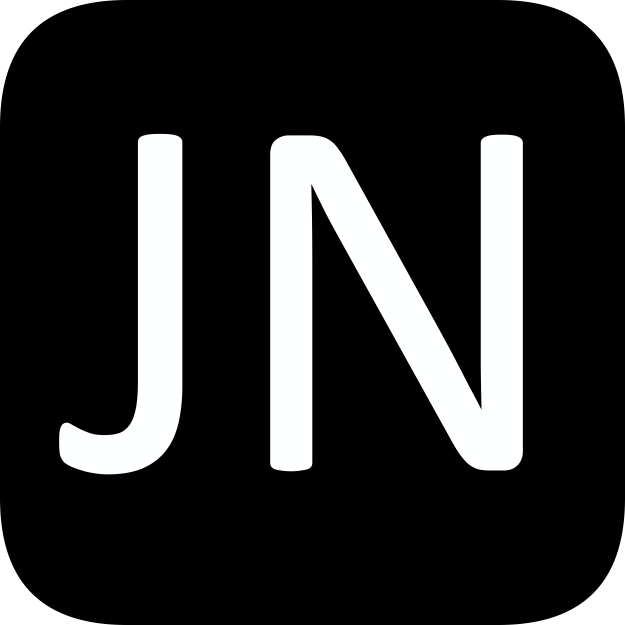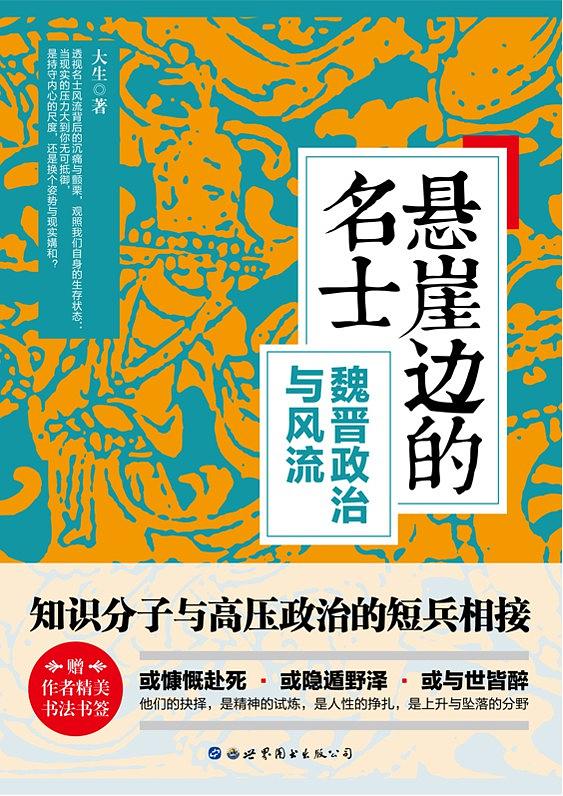
魏晋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时代,是中华文明几千年里难得的文化盛世。由于魏晋知识分子都是世家大族,因此这个时期又具有独特的贵族气质。当人们不再为了生计担忧,也没有隋唐后科举的桎梏,就有更多的闲情逸致去思考一些形而上的东西,这恰恰是哲学思辨滋生的土壤。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就在这自由的思辨中建立起来。
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?而且我也有答案,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,那就是:“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。”所谓不理智的年代,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,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,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;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,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。我认为,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,假如不讲理,他就没有长处,只有短处,活着没意思,不如死掉。
——王小波《知识分子的不幸》
自汉代以来,我们这个国家就一直在思想上不断钳制知识分子,从罢黜百家,到科举取士,再到宇宙真理。这是统治者最舒服的方式,也是知识分子最痛苦的方式。这样的后果就是知识分子沦为唱赞歌和无病呻吟的御用文人,更丧失了独立的精神。皇权越集中的时代,对知识分子的钳制也越厉害,而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段皇权与士族门阀共治的时期,这就给了知识分子难得且有限的自由空间。在汉代,儒家经学是保障政治稳定的理论武器,但汉末三国的混乱使得它不再那么无懈可击,这让知识分子开始自发的反思,不再拘泥于教条主义,开始重新审视这些圣人的观点,这便开启了魏晋玄学思辨的时代。
一段历史中,最吸引人的,最让人喜欢的还是那些特里独行又才华四溢的人。
魏晋最耀眼的明星当属曹子建,他应该算是拥有上帝之手的人,属于一生都在复现“文章本天成,妙手偶得之”的人。“翩若惊鸿,婉若游龙,荣曜秋菊,华茂春松……轻云蔽月,流风回雪”这怎么可能是凡夫俗子能写的出的。也难怪王士祯感叹“ 汉魏以来,二千余年间,以诗名其家者众矣。顾所号为仙才者,唯曹子建、李太白、苏子瞻三人而已。”曹植本意是想辅佐明主,建立功业,但身为皇族,一生受到兄弟、侄子的怀疑和监禁,在得知曹丕篡汉的时候,还为汉朝的灭亡大哭了一场。他是天真的,天真的不适合搞政治,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现实的艾怨带进诗歌,他的诗歌一直给人向上的力量。
说到魏晋,肯定绕不过竹林七贤,更绕不开嵇康,而他也成为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代表。在司马氏篡权之后,自知得国不正,就打着儒家礼教、仁义道德的旗号打击异见者,首当其冲的就是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论派。伪君子治国当然招来的也是一群附和的伪君子,而真正的君子当然为他们所不容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嵇康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公开羞辱司马氏政权的行为才显得如此高大。
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谈过魏晋禅代的不同。
曹之代汉,司马氏之代魏,其迹虽同,而势力尚有不同者……尝推其故,操当汉室大坏之后,起义兵,诛暴乱,汉之臣如袁绍、吕布、刘表、陶谦等能与操为敌者,多手自削平,或死或诛,其在朝者不过如杨彪、孔融等数文臣,亦废且杀,其余列侯将帅皆操所擢用,虽前有董承、王子服、吴子兰、种辑、吴硕,后有韦晃、耿纪、金韦,欲匡汉害操,而皆无兵权,动辄扑灭,故安坐邺城,而朝政悉自己出。
司马氏则当文帝、明帝国势方隆之日,猝遇幼主嗣位,得窃威权,其时中外臣工尚皆魏帝所用之人,内有张缉、苏铄、乐敦、刘贤等伺隙相图,外有王陵、毋邱俭、诸葛诞等相继起兵声讨,司马氏惟恃挟天子以肆其奸,一离京辇,则祸不可测,故父子三人执国柄,终不敢出国门一步,亦时势使然也。
然操起兵于汉祚垂绝之后,力征经营,延汉祚者二十余年,然后代之。司马氏当魏室未衰,乘机窃权,废一帝,弑一帝,而夺其位,比之于操,其功罪不可同日语矣。
可见西晋的建国缺乏合法性,因此开国之臣多为趋炎附势之徒,普遍缺乏政治信念,也没人真的尊重司马氏。这时的西晋上下充斥着奢侈的风气,知识分子普遍缺乏信念,只追求钱和享乐。魏晋之际的正始、竹林名士是有很高的文学和哲学水平的,他们的狂狷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。而到了西晋,为了模仿竹林七贤,一群人也搞了“四友”、“八达”等所谓的名士集团,却缺乏正始、竹林名士深刻的思想性,只学得个形似神不似,徒留笑柄,真可谓真风告逝,大伪斯兴。西晋建国没多久就遇到了司马衷和贾南风两个极品,然后八王之乱西晋灭亡,也算是对司马氏的报应。在这一片大伪之风中,也存有几丝难得的真性情,比如闻鸡起舞、鏖战中原的刘琨、祖逊;“ 吾虽不杀伯仁,伯仁由我而死。幽冥之中,负此良友!”的周伯仁;士大夫理想化身的谢安;还有,在权臣桓温死后独自前去祭拜的顾恺之。如鲁迅所说“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,少有韧性的反抗,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,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;见胜兆则纷纷聚集,见败兆则纷纷逃亡。”正是这样,这些人才能称得上真名士。